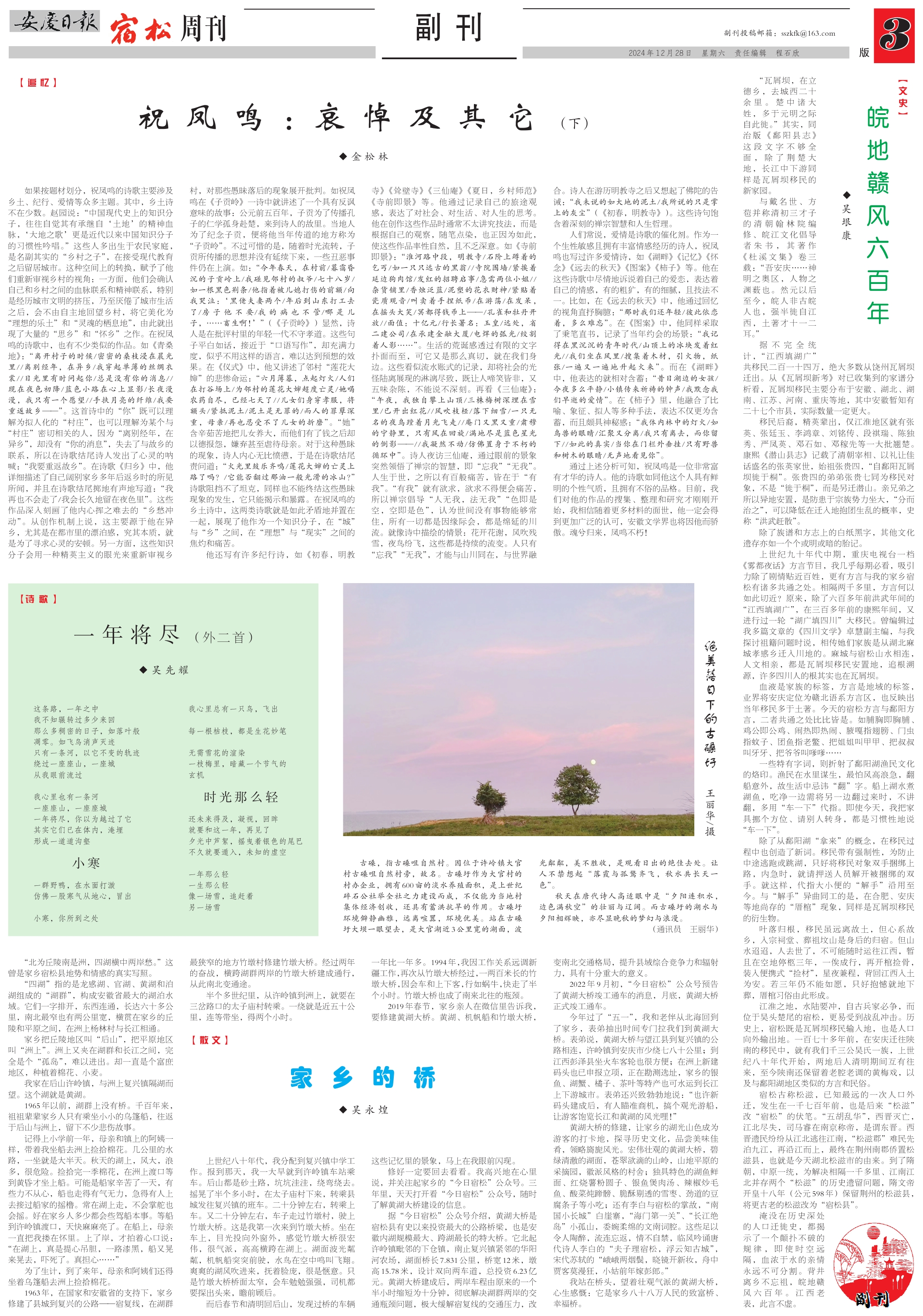

祝凤鸣:哀悼及其它(下)
◆金松林
如果按题材划分,祝凤鸣的诗歌主要涉及乡土、纪行、爱情等众多主题。其中,乡土诗不在少数。赵园说:“中国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往往自觉其有承继自‘土地’的精神血脉,‘大地之歌’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习惯性吟唱。”这些人多出生于农民家庭,是名副其实的“乡村之子”,在接受现代教育之后留居城市。这种空间上的转换,赋予了他们重新审视乡村的视角:一方面,他们会确认自己和乡村之间的血脉联系和精神联系,特别是经历城市文明的挤压,乃至厌倦了城市生活之后,会不由自主地回望乡村,将它美化为“理想的乐土”和“灵魂的栖息地”,由此就出现了大量的“思乡”和“怀乡”之作。在祝凤鸣的诗歌中,也有不少类似的作品。如《青桑地》:“离开村子的时候/密密的桑枝浸在晨光里//离别经年,在异乡/我穿起单薄的丝绸衣裳//日光里有时问起你/总是没有你的消息//现在夜色初降/蓝色小路在心上显影/长夜漫漫,我只有一个愿望//手扶月亮的纤维/我要重返故乡——”。这首诗中的“你”既可以理解为拟人化的“村庄”,也可以理解为某个与“村庄”密切相关的人,因为“离别经年,在异乡”,却没有“你的消息”,失去了与故乡的联系,所以在诗歌结尾诗人发出了心灵的呐喊:“我要重返故乡”。在诗歌《归乡》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阔别家乡多年后返乡时的所见所闻,并且在诗歌结尾掷地有声地写道:“我再也不会走了/我会长久地留在夜色里”。这些作品深入刻画了他内心挥之难去的“乡愁冲动”。从创作机制上说,这主要源于他在异乡,尤其是在都市里的漂泊感,究其本质,就是为了寻求心灵的安顿。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会用一种精英主义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乡村,对那些愚昧落后的现象展开批判。如祝凤鸣在《子贡岭》一诗中就讲述了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故事:公元前五百年,子贡为了传播孔子的仁学孤身赴楚,来到诗人的故里。当地人为了纪念子贡,便将他当年传道的地方称为“子贡岭”。不过可惜的是,随着时光流转,子贡所传播的思想并没有延续下来,一些丑恶事件仍在上演。如:“今年春天,在村前/暮霭昏沉的子贡岭上/我碰见邻村的叔爷/七十八岁/如一根黑色荆条/他指着被儿媳打伤的前额/向我哭泣:‘黑佬夫妻两个/年后到山东打工去了/房子他不要/我的病也不管/哪是儿子,……畜生啊!’”(《子贡岭》)显然,诗人是在批评村里的年轻一代不守孝道。这些句子平白如话,接近于“口语写作”,却充满力度,似乎不用这样的语言,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在《仪式》中,他又讲述了邻村“莲花大婶”的悲惨命运:“六月薄暮,点起灯火/人们在打谷场上/为邻村的莲花大婶超度亡灵/她喝农药自尽,已经七天了//儿女们身穿孝服,将额头/紧抵泥土/泥土是无罪的/而人的罪孽深重,母亲/再也忍受不了儿女的折磨”。“她”含辛茹苦地把儿女养大,而他们有了钱之后却以德报怨,嫌弃甚至虐待母亲。对于这种愚昧的现象,诗人内心无比愤懑,于是在诗歌结尾责问道:“火光里鼓乐齐鸣/莲花大婶的亡灵上路了吗?/它能否翻过那油一般光滑的冰山?”诗歌阻挡不了坦克,同样也不能终结这些愚昧现象的发生,它只能揭示和暴露。在祝凤鸣的乡土诗中,这两类诗歌就是如此矛盾地并置在一起,展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城”与“乡”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焦灼和痛苦。
他还写有许多纪行诗,如《初春,明教寺》《耸壁寺》《三仙庵》《夏日,乡村师范》《寺前即景》等。他通过记录自己的旅途观感,表达了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思考。他在创作这些作品时通常不太讲究技法,而是根据自己的观察,随笔点染,也正因为如此,使这些作品率性自然,且不乏深意。如《寺前即景》:“淮河路中段,明教寺/石阶上蹲着的乞丐/如一只只远古的黑翁//寺院围墙/紧挨着延边狗肉馆/发红的招聘启事/急需两位小姐//杂货铺里/香烛泛蓝/泥塑的花衣财神/紧贴着瓷质观音/叫卖着手捏纸币/在游荡/在发呆,在摇头大笑/冥都得钱币上——/孔雀和牡丹开放//面值:十亿元/行长署名:玉皇/远处,省二建公司/在承建金融大厦/电焊的弧光/绞割着人影……”。生活的荒诞感透过有限的文字扑面而至,可它又是那么真切,就在我们身边。这些看似流水账式的记录,却将社会的光怪陆离展现的淋漓尽致,既让人啼笑皆非,又五味杂陈,不能说不深刻。再看《三仙庵》:“午夜,我独自攀上山顶/三株梅树深埋在雪里/已开出红花//风吹枝桠/落下细雪/一只无名的夜鸟蹚着月光飞走//庵门又黑又重/肃穆的宁静里,只有风在回旋/满地尽是蓝色星光的倒影——//我凝然不动/仿佛置身于不朽的循环中”。诗人夜访三仙庵,通过眼前的景象突然领悟了禅宗的智慧,即“忘我”“无我”。人生于世,之所以有百般痛苦,皆在于“有我”。“有我”就有欲求,欲求不得便会痛苦,所以禅宗倡导“人无我,法无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认为世间没有事物能够常住,所有一切都是因缘际会,都是绵延的川流。就像诗中描绘的情景:花开花谢,风吹残雪,夜鸟纷飞,这些都是持续的流变。人只有“忘我”“无我”,才能与山川同在,与世界融合。诗人在游历明教寺之后又想起了佛陀的告诫:“我未说的如大地的泥土/我所说的只是掌上的灰尘”(《初春,明教寺》)。这些诗句饱含着深刻的禅宗智慧和人生哲理。
人们常说,爱情是诗歌的催化剂。作为一个生性敏感且拥有丰富情感经历的诗人,祝凤鸣也写过许多爱情诗,如《湖畔》《记忆》《怀念》《远去的秋天》《图案》《柿子》等。他在这些诗歌中尽情地诉说着自己的爱恋,表达着自己的情感,有的粗犷,有的细腻,且技法不一。比如,在《远去的秋天》中,他通过回忆的视角直抒胸臆:“那时我们还年轻/彼此依恋着,多么难忘”。在《图案》中,他同样采取了秉笔直书,记录了当年约会的场景:“我记得在黑沉沉的青年时代/山顶上的冰块发着红光//我们坐在风里/搜集着木材,引火物,纸张/一遍又一遍地升起火来”。而在《湖畔》中,他表达的就相对含蓄:“昔日湖边的女孩/今夜多么平静/小镇传来祈祷的钟声/我默念我们早逝的爱情”。在《柿子》里,他融合了比喻、象征、拟人等多种手法,表达不仅更为含蓄,而且颇具神秘感:“我体内林中的灯火/如鸟兽的眼睛/汇聚又分离/我只有离去,而你留下//如此的真实/当你在门栏外垂挂/只有野兽和树木的眼睛/无声地看见你”。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祝凤鸣是一位非常富有才华的诗人。他的诗歌如同他这个人具有鲜明的个性气质,且拥有不俗的品格。目前,我们对他的作品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才刚刚开始,我相信随着更多材料的面世,他一定会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安徽文学界也将因他而骄傲。魂兮归来,凤鸣不朽!
江苏路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仅提供技术服务支持, 文字、图片、视频版权归属发布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