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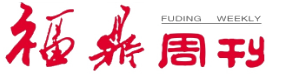
水澳堡百年荣光何处寻

一
在我老家周边十里八村临海渔村中,唯独她没有我寒窗苦读的同学,但她与我的关系,却超越了其他村庄。究其原因,是因为那里不仅与我家乡相邻最近,有我最小的妹妹嫁到那里,还因为有一支同宗共祖的族人,这样一种多层次关系,必然在我内心里积淀起一种特殊的情分。我说的这个“她”,就是水澳。一座曾在《福鼎旧志集》中被称作“大白鹭东五里”的水澳堡,“明洪武二年置福宁卫军防守。《州志》作水屿堡”。
水澳村地处我市东南方向沿海,隶属于沙埕镇辖区,东接官城,西邻白鹭,北靠青山,南面大海。村庄坐北朝南,分城内城外,村居海岸礁岩耸立,海水漫涌环绕,有几处岩礁突出如屏障,形成一个天然小内港,远望如半岛,村落地理环境独具特色,村民多以渔业为生。回溯历史,水澳堡建于明洪武初期,彼时倭寇在闽浙沿海一带出没,明朝下诏“闽浙沿海造海舟防倭,海防戒备始之。”洪武二年设巡检司于水澳,由旧桐山司徙驻,正式开启了百多年驻防东海边地一隅,至明正德年间才徙于芦门,即今管阳沈青。《福宁州志》万历版留下“古寨之水澳,在十二都”的记载,寥寥可数不到十个字,却是一部闪耀着荣光的煌煌史迹。
纵观明代史料,从北到南,沿海多有海患的记载。如 “洪武三年是月(辛巳日),倭寇山东、浙江、福建滨海州县。”(《明史》第三章) “十七年壬戌,汤和巡视沿海诸城防倭。”(《明史》第五章)“二十年夏四月戊子,江夏侯周德兴筑福建濒海城,练兵防倭。”(同上)《明史》还记载:永乐十五年,“败倭寇于金乡卫。”明代时金乡卫是著名的抗倭重镇,明军在金乡卫地区有几次成功抗击倭寇的重要作战记录:永乐十五年,即公元1417年,内官张谦出使西洋返回途中,行至浙江金乡卫补给时,遭遇大股倭寇。明军在金乡卫海域与倭寇展开激战,最终取得了胜利,捕获倭寇数十人,并将其押送至京师。永乐十八年,即公元1420年,倭寇再次进犯金乡卫及周边地区,进行扰掠活动,彼时当地明军迅速响应,成功击退了倭寇,保障了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嘉靖年间,戚继光曾多次在金乡卫扎营练兵,加强防御力量,戚家军在金乡卫一带进行了多次抗倭作战,取得了显著的战果,摧毁了倭寇的多个据点,包括横屿倭寇老巢。水澳离金乡不远,不知这些海战有没有波及。但历史如果有记忆,一定会记得发生在明嘉靖四十三年的那一场海战,这也是网上流传着一个明代时期关于水澳的一场海战。
那是公元1564年,四月二十一日,那一天的天气应该也像现在这样,阳光明媚,风平浪静,在春夏交替之际,正是海上捕鱼的大好季节,水澳村渔民应当是驾船出海,撒网捕鱼,那一网网活蹦乱跳的鱼鲜海货,正在渔民们的手中起网,他们的脸上应该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之情。然而,这一天的情景却不是这样,水澳村好像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村里已人去城空。突然海面炮火震天,倭巢火光四起,倭寇哀声遍野。原来,这是福宁北路守备李超,在戚继光指挥下来平倭的,官军围剿水澳西路残余倭寇,军用火箭、鸟铳一齐发射。福宁军民奋勇拼杀,战斗十分惨烈。不到几个时辰,官军便捣毁了倭巢,地方被掳百姓获救无数,抗倭战斗又取得一次重大胜利。
二
何止是一场海战。
海疆广阔,绵延万里。海水抵达的地方,或多或少,都有着不一样的人文景观,也可能留下一般的传奇。特别是在那些倭寇蜂涌的年代。而嘉靖年间所发生的,或许只是水澳人一代又一代人口口相传的故事之一,但经历过明末清初海禁与迁界的过程,水澳堡已沉寂了多少年,直至清康熙二十年朝廷下诏复界,原住民早已远走他乡,曾经的古城堡或分崩离析,或深埋于荒草之中,后来者迁入已是乾隆年间的事,而发生在明代海战的事,估计没有几个人会知道,有的也只是根据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传说故事,套在村史上。无论是线下查阅《福宁州志》还是《福宁府志》,上网查阅及询问AI,给出的答案或查无史实,或未有直接记载,都无法予以证实。当然,明朝时的水澳堡,地处沿海,直面倭患,在嘉靖四十三年这一时间节点上,一定曾遭遇过倭寇的侵扰,发生过或大或小的海战,在我看来,它或许是真实的,然而时过境迁,我们只能在岁月的回望中,一次次去想象那些参加“抗击倭寇,保家卫国”的将士,在惨烈战场上光荣历史,细细品味时光留下的血痕与印记。
现在回过头来关注水澳村建城堡,历史距今已逾六百五十多年。洪武初期,明朝政府为应对闽浙沿海倭寇劫掠与滋扰,在从北到山东,南到广东沿海一线,加强海疆防御。其实早在宋代,闽海就多有海寇横行。《三山志》有载:“嘉祐八年,提刑司奏:长溪、耀江、宁德、连江、长乐、福清六县皆边海,盗贼乘船出没,乃添置沿海六县巡检一员,于长溪造刁渔船十只,往来海上收捕。”宋李纲《札略》中说:“臣契勘广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官司不能讨捕,帅司无战船、水军,寇至坐视猖獗,濒海之民罹其荼毒。”《明史》记载:“洪武五年,命浙、福造海舟防倭”。水澳即从此建城筑堡,城堡建成之后,即移桐山巡检司于此。巡检司是周德兴入闽抗倭于要害之地增设的军事后备基地,其作用在于平日巡逻缉捕奸宄,如果有军情就会同正规官军作战,相互照应支援,互动联络,壮大声势,以更有力地打击倭寇势力。明史上的几个时间节点,可以说明其抗倭的光荣历程,展示明时军民同仇敌忾的精神风采。
如《明史》:“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命江夏侯周德兴抽福建福、兴、漳、泉四府三丁之一为沿海戍兵,得万五千人。移置卫所,于要害处筑城十六。”又《明史》:“周德兴至闽,按籍佥练,得民兵十万余人。相视要害,筑城一十六,置巡司四十有五,防海之策始备”。《明史》:“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又命汤和行视闽粤,筑城增兵,置福建沿海指挥使司五,曰:福宁、镇东、平海、永宁、镇海。”彼时水澳堡巡检司隶属于福宁卫,福建地分三路,以福宁为北路,管辖福宁卫所军并陆营兵、烽火和小埕二寨。《明史》:“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令滨海卫所,每百户及巡检司皆置船二,巡海上盗贼。”《明史》记载都御史王询言:“闽之势,福宁,北路之要害也,贼自台、温来者,必犯之。”《筹海图编》记载:“嘉靖二十七年戊申三月,都御史朱纨以都司卢镗帅福清兵船泊温州之海门,把总俞亨统燕山兵船协助之,以备福宁之北境海道。”《明史》:“嘉靖四十三年,巡抚谭纶疏言:‘五寨守扼外洋,法甚周,悉宜复旧制。以烽火门、南日、浯屿二䑸为正兵,铜山、小埕二䑸为游兵。寨设把总,分汛地,明斥堠,严会哨。改三路参将为守备,分新募浙兵为二班,各九千人,春秋番上。各县民壮皆补精悍,每府领以武职一人。兵备使者以时阅视。皆从之。’”说明当时福建海防形势之严峻,可见一斑。而各地巡检司设有兵马,称弓兵,或称机兵,其组织在《明史》中说“有司训练,遇警调发,给以行粮。”据说,一个司弓兵一般设60、70人或100人不等,大部分是本地沿海渔民,由附近海澳招募扩充人员。当时招募一个弓兵与田赋挂钩,民间也有私自雇人差役,要付双倍的银两。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倭寇入侵,因这些弓兵大多是本地居民无力抗警,政府只好对司中弓兵人员进行裁减,每司只留弓兵16名,给银五两六分一厘五毫,把其余征得的赋税充作军饷,这样大大提高了士兵作战的战斗力。
三
历史上,水澳曾为福鼎乃至闽海之紧要澳口,与白鹭汛仅一步之遥,与沙埕、南镇、黄崎、烽火门、三沙相通,并形成掎角之势,陆地距南镇汛二十五里,水路距沙埕汛四十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历为兵家所倚重,水澳城堡由此得以兴筑,城设东、南、西、北四个城门,依山岛而建形成环卫形,城堡坐北朝南,向小澳湾。东门门宽1.4米、深1.3米、高2米,门内到地面总高3米,为方形门,门旁有两个门柱柱础,门旁置一米余宽的小道。东门面朝大海,对面就是冬瓜屿。西门宽一米六、门深一米七、高近四米,为拱形门。置女墙高六十厘米、厚七十厘米、城墙厚一点四米。北门于1993年重修,门高三米五。城墙总长近一千二百米,按地形而修筑最高达十六米多,低处也有六米多,总建筑面积达十余万平方米,现城墙总存二百余米。明正德年间,水澳巡检司徙驻管阳沈青葫芦门,嘉靖末年仍旧徙于桐山。乾隆四年,即公元1739年,福鼎置县,县治设在桐山,遂移巡检司于霞浦,称为柘洋司。
水澳村前有一座岛屿如屏横列,守护着白鹭湾海域。《福宁府志》之“地理志·山川”记载:“屏风山在白鹭外海中,状如屏,赖以障黄崎而卫水澳”。《福鼎旧志集》也记载“屏风山”之条目“坐落于水澳东南方向外海上,横列于水澳之前如屏障,并与之相向坐望”。屏风山乃是冬瓜屿旧名,俗称荡山,因形似冬瓜而名之,是周边沿海最大的岛屿。相传在宋元年间,就有人在此生活,元朝末年,海寇入侵劫掠,居民四散逃逸。留下房舍、寺庙等残垣断壁,和一些杂草丛生的农地。现在,冬瓜屿岛上还建有码头和简易道路,供人上岛游玩。清统一海疆后,尤其是自雍正以来,闽海平定,水澳陆续有外氏迁入,先后有施、吴、高、柯、曾、董、蔡、陈、王等族入住堡内,他们多以海为生,以渔为业,随着朝代更替,时间推移,社会稳定,村民安居,村居获得繁荣发展,最多时人口达到2000多人。
据说在乾隆年间,盘踞在嵛山的海盗以近百艘船的强势之劲来攻水澳,以期掠夺渔民财物。甚至在民国时期、解放初期,水澳还时常遭受日本海盗和盘踞在七星岛上的海贼的扰攘,他们在澳上横行霸道,敲诈勒索。水澳城堡再次奋起反击,清乾隆时,就从秦屿烽火营运回十门土炮,以松木作支架,安放于各城门头,给敌方以强大的威慑。海盗见水澳防守严密,无法取胜,就盘踞于冬瓜屿,以伺时机。面对海盗虎视眈眈,水澳村民加紧防守,团结一致,英勇抗击,可见一斑。
一座城堡因为一个朝代的海防抗倭而成就她的英名,一座城堡因为从一群人到一代代人的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而谱写一段非凡的史诗。水澳堡在那些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自己的使命,为保卫家园,捍卫民族尊严而生存。
□ 董欣潘/文 刘超超/图
江苏路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仅提供技术服务支持, 文字、图片、视频版权归属发布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