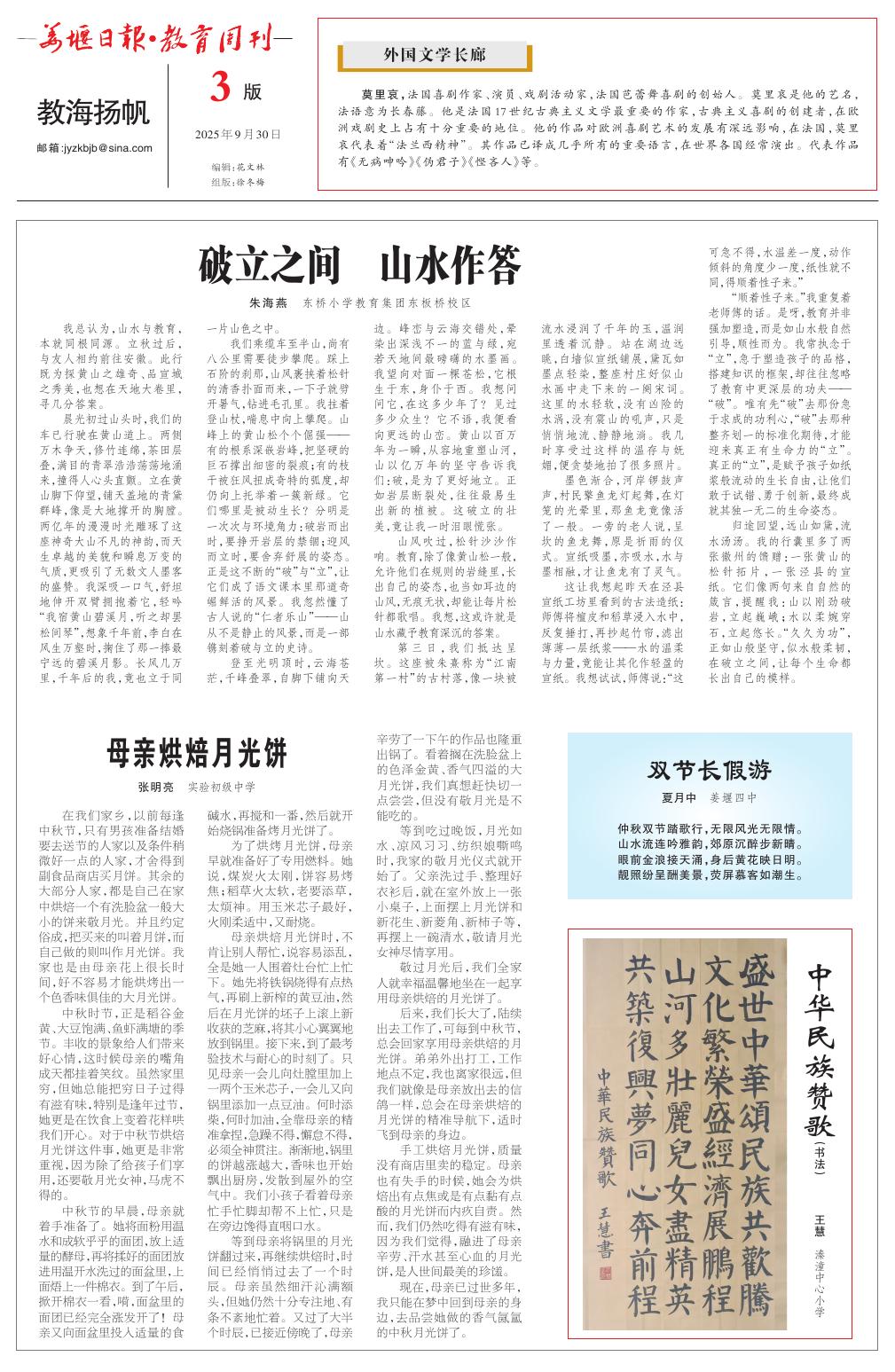

破立之间 山水作答
朱海燕 东桥小学教育集团东板桥校区
我总认为,山水与教育,本就同根同源。立秋过后,与友人相约前往安徽。此行既为探黄山之雄奇、品宣城之秀美,也想在天地大卷里,寻几分答案。
晨光初过山头时,我们的车已行驶在黄山道上。两侧万木争天,修竹连绵,茶田层叠,满目的青翠浩浩荡荡地涌来,撞得人心头直颤。立在黄山脚下仰望,铺天盖地的青黛群峰,像是大地撑开的胸膛。两亿年的漫漫时光雕琢了这座神奇大山不凡的神韵,而天生卓越的美貌和瞬息万变的气质,更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的盛赞。我深吸一口气,舒坦地伸开双臂拥抱着它,轻吟“我宿黄山碧溪月,听之却罢松间琴”,想象千年前,李白在风生万壑时,掬住了那一捧最宁远的碧溪月影。长风几万里,千年后的我,竟也立于同一片山色之中。
我们乘缆车至半山,尚有八公里需要徒步攀爬。踩上石阶的刹那,山风裹挟着松针的清香扑面而来,一下子就劈开暑气,钻进毛孔里。我拄着登山杖,喘息中向上攀爬。山峰上的黄山松个个倔强——有的根系深嵌岩峰,把坚硬的巨石撑出细密的裂痕;有的枝干被狂风扭成奇特的弧度,却仍向上托举着一簇新绿。它们哪里是被动生长?分明是一次次与环境角力:破岩而出时,要挣开岩层的禁锢;迎风而立时,要舍弃舒展的姿态。正是这不断的“破”与“立”,让它们成了语文课本里那道奇崛鲜活的风景。我忽然懂了古人说的“仁者乐山”——山从不是静止的风景,而是一部镌刻着破与立的史诗。
登至光明顶时,云海苍茫,千峰叠翠,自脚下铺向天边。峰峦与云海交错处,晕染出深浅不一的蓝与绿,宛若天地间最磅礴的水墨画。我望向对面一棵苍松,它根生于东,身仆于西。我想问问它,在这多少年了?见过多少众生?它不语,我便看向更远的山峦。黄山以百万年为一瞬,从容地重塑山河,山以亿万年的坚守告诉我们:破,是为了更好地立。正如岩层断裂处,往往最易生出新的植被。这破立的壮美,竟让我一时泪眼慌张。
山风吹过,松针沙沙作响。教育,除了像黄山松一般,允许他们在规则的岩缝里,长出自己的姿态,也当如耳边的山风,无痕无状,却能让每片松针都歌唱。我想,这或许就是山水藏予教育深沉的答案。
第三日,我们抵达呈坎。这座被朱熹称为“江南第一村”的古村落,像一块被流水浸润了千年的玉,温润里透着沉静。站在湖边远眺,白墙似宣纸铺展,黛瓦如墨点轻染,整座村庄好似山水画中走下来的一阕宋词。这里的水轻软,没有凶险的水涡,没有震山的吼声,只是悄悄地流、静静地淌。我几时享受过这样的温存与妩媚,便贪婪地拍了很多照片。
墨色渐合,河岸锣鼓声声,村民擎鱼龙灯起舞,在灯笼的光晕里,那鱼龙竟像活了一般。一旁的老人说,呈坎的鱼龙舞,原是祈雨的仪式。宣纸吸墨,亦吸水,水与墨相融,才让鱼龙有了灵气。
这让我想起昨天在泾县宣纸工坊里看到的古法造纸:师傅将檀皮和稻草浸入水中,反复捶打,再抄起竹帘,滤出薄薄一层纸浆——水的温柔与力量,竟能让其化作轻盈的宣纸。我想试试,师傅说:“这可急不得,水温差一度,动作倾斜的角度少一度,纸性就不同,得顺着性子来。”
“顺着性子来。”我重复着老师傅的话。是呀,教育并非强加塑造,而是如山水般自然引导,顺性而为。我常执念于“立”,急于塑造孩子的品格,搭建知识的框架,却往往忽略了教育中更深层的功夫——“破”。唯有先“破”去那份急于求成的功利心,“破”去那种整齐划一的标准化期待,才能迎来真正有生命力的“立”。真正的“立”,是赋予孩子如纸浆般流动的生长自由,让他们敢于试错、勇于创新,最终成就其独一无二的生命姿态。
归途回望,远山如黛,流水汤汤。我的行囊里多了两张徽州的馈赠:一张黄山的松针拓片,一张泾县的宣纸。它们像两句来自自然的箴言,提醒我:山以刚劲破岩,立起巍峨;水以柔婉穿石,立起悠长。“久久为功”,正如山般坚守,似水般柔韧,在破立之间,让每个生命都长出自己的模样。
江苏路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仅提供技术服务支持, 文字、图片、视频版权归属发布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