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间记》
序章·灶启
腊月廿八的晨光斜切入厨房时,砂锅正发出轻快的咕嘟声。祖母掀盖的刹那,白汽如游龙窜上吊柜,扑灭了窗台那枝孤零零的腊梅香。我蜷在烤箱前屏息凝神,看面糊在玻璃门后舒展腰肢,围裙沾的面粉结成了北境地图。突然"滋啦"一声异响,母亲举着铜勺冲进来:"蛋糊淌到发热管了!"黑烟从烤箱缝隙窜出,惊得父亲偷捞排骨的手一抖,油星子溅在褪色的"灶君图"上,爷爷的笑声震得墙头挂历哗啦作响,惊醒了檐下打盹的麻雀。
一、焦香札记
第三个失败的蛋糕蜷在青花瓷盘里,焦褐裂纹恰似龟甲占卜的纹路。祖母用竹筷轻戳表面:"硬过你爸当年挖的冻土豆。"说着掰碎泡进排骨汤,瓷勺搅动时,浮沉的蛋糕渣竟像极了《山海经》里记载的旋龟。窗外的麻雀倒是爱极了这份焦香,祖父撒向晾衣绳的面包屑被晨风谱成五线谱。最胆大的那只灰羽雀儿,常趁我开窗时跃进厨房,歪头打量料理台上的电子秤,黑豆似的眼珠映着烤箱红光,俨然成了我的监工。
子时的厨房亮着偷溜进来的月光,冰箱贴上的便利贴早被蒸气熏得卷了边。当第十次试验终于烤出蓬松的云朵,裂纹在表面拼成歪嘴笑脸。祖父用牙签戳起薄荷叶插在顶端:"灶王爷也该换换口味啦。”

二、长桥偶书
年初九的西湖裹着青灰棉袍,长桥的石栏沁着隔夜寒露。卖麦芽糖的老伯敲响铜刀,叮当声里裹着吴语温软:"学生妹来块甜的,抵得过三斤西北风。"琥珀色的糖块在冷空气中碎裂,清甜即刻在舌尖结晶。
忽有琵琶裂帛,循声望去,几位穿绀青夹袄的妇人正在亭中排演。领头那位鬓角银丝微颤,水袖抛出的弧线惊散桥头寒雀。"小姑娘帮我们拍段抖音可好?"她递来的手机壳上还沾着桂花香,想来是常去满觉陇采风的票友。
后退取景时布鞋跟卡进石缝青苔,踉跄间险些撞翻老伯的糖车。阿姨们笑作一团,往我兜里塞满冬瓜糖:"比你们小年轻喝的珍珠奶茶实在。"湖风掀起她们的丝巾,十几条彩绸在铅灰天色里翻飞,倒比盛夏的接天莲叶更鲜活。拍完视频正要道谢,却见她们对着手机屏幕惊呼:"哎呀,把雷峰塔的塔尖拍歪了!"原来塔影正斜斜映在领头阿姨的珍珠发夹上,倒比端正取景更添三分意趣。
三、洇香记
临行前夜,母亲将保温桶裹成襁褓。三层保鲜膜缠紧后还要系上红绳:"上车后放脚下,千万别晃!"可列车刚过临平南,一缕醇厚的肉香便悄然渗出。汤汁在帆布包底洇出暗色云纹,渐渐漫成雷峰塔顶的雨积云。
邻座织毛线的阿姨忽然倾身:"家里炖的排骨?"不等我赧然解释,她已变戏法般掏出梅子酱玻璃罐。褪色的"福"字贴纸下,隐约可见"2008春运留念"的铅笔字。"去年我闺女带红烧肉也漏汤。"她利索地帮我转移汤水,织针在毛线团里划出流星轨迹,"现在的保鲜盒啊,不如老罐子知冷知热。"
罐口白雾袅袅升起时,她忽然轻笑:"我家丫头头回离家,酱鸭漏了半箱子,在虹桥站抱着行李箱直跺脚。"玻璃罐递来时带着她的体温,螺纹口还沾着经年的梅子香。我摩挲着罐身细小划痕,忽觉这分明是份流动的家谱——不知多少游子的行囊在此寄存过乡愁。
终章·岁暖
此刻烤箱仍哼着寒假里练就的老调,砂锅里新添的排骨汤咕嘟冒泡,白雾在玻璃窗上勾画着旧日图案。祖母忽然轻呼,却见那胆大的灰羽雀儿又在啄食窗台,尾羽沾着今晨新落的霜,倒是与晾衣绳上飘荡的面包屑遥相呼应。
昨夜整理书包夹层,翻出半块风化的冬瓜糖。糖纸上的"吉祥如意"已褪成水痕,甜味却固执地渗进日记本的横线格,竟将《寒假趣事儿》的标题染出蜜色。那些烤焦的晨昏、洇湿的黄昏、陌生人袖口抖落的暖,都在结霜的玻璃上凝成童稚涂鸦——歪扭的蛋糕轮廓旁,歪斜地写着"180℃不是死数",洇开的汤汁印迹里,依稀能辨雷峰塔的剪影。
忽而想起长桥边老伯的铜刀敲糖声,叮叮当当惊碎了湖面的寒雾。那些零落的麦芽糖渣,大约已化作早樱的养料;阿姨们遗落的丝巾,或许正裹着哪棵瑟瑟发抖的冬青。而此刻掌心的玻璃罐里,梅子香早被肉汤浸润,螺纹口的划痕却愈发温润,倒像是被无数个相似寒假的掌心摩挲出的包浆。
冰箱贴上的便利贴又换了新颜:"蛋糕放中层,砂锅用文火。"字迹被蒸气熏得微潮,恰似西湖那日的雨雾。原来所谓年味,不过是灶王爷偷闲打盹的须臾,容我们将人间烟火,一瓢一饮地藏进衣襟袖底,待岁月风干后,竟成了生命里永不褪色的水印。
教师教育学院 张佳妮18061958216

荠
一年回故乡两次,一次在寒假,一次在暑假。
今年是寒假,待的时间稍短些,却也郑重,因为适逢春节。而按照父母本家轮换的次序,我住在祖母家。
祖母的房子在巷子的深处,要走过一面大岩石墙,趟过一条小碎石路。幼时的我不爱走这崎岖的路,总习惯掂着脚尖,试图在那凹凸的石路上找到一两个平坦的着陆点,蹦着跳着,张牙舞爪到路的尽头。母亲为此总笑我,而曾祖母常会护着我,昵称我“小燕子”,全家里也只有她会这么唤我。
“哎呦呦,我的乖囡囡,可爱的小燕子……”
曾祖母住在祖母家的二楼,喜欢坐在大露台里,往往看到有小姑娘经过,她就会兴奋地喊起来——万幸,今天我回来了。
如今的我依然不爱走那条碎石路,却也再没机会重新感受脚底在石子上战栗的触觉——水泥封睡了碎石,闪闪亮的是平整的新时代的产物。却也只是相隔了半年的时光啊。其实,应该是有先兆的,当大岩石墙上的幼时刻画渐渐斑驳,当藤蔓侵蚀石缝愈发昌盛不衰,我部分的时光和记忆只能沉默地不再行进。
唯一令我欣喜的,许是施工人员的浇灌不匀,许是这小生命的顽强——石墙和路的交汇处,竟汪着一捧小小的地米菜,细柄,纤茎,心形的果,米白的花,嫩嫩地摇曳在尘埃里。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曾祖母爱这怜怜的春天生灵,我自然爱屋及乌。
“她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荠……”
荠常常是我们家春节的特邀嘉宾——曾祖母总会用一段谜语诗引出她,“寻药踏青采嫩芽,能蔬可牧利农家。 溪头翠叶春花白,羡煞城中桃李花。”每每看到大人们不懂真知而云里雾里的模样,我便暗自得意——这是我和曾祖母的小秘密,“是荠,是荠呀……”我常常大声喊着,是荠听到都要羞得半遮面的程度,也幸而她听不到,也幸而她还在。
曾祖母跟荠是过命的交情——大饥饿的年代,荠勤勤恳恳地养活了她一半的孩子,而在大和平的岁月里,依然丰丰饶饶了她最爱的曾孙女的童年。
我清楚地记得,曾祖母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在二楼厨房旁的小小房间里做手工活——她被岁月的贫瘠固化了,到该想天伦的年纪也依旧不放过任何赚取钱财傍身的机会。曾祖父想陪着她,帮她一起做活计,却总是被赶出去,只有我,也只有笨手笨脚的我厚着脸皮喊也喊不走——惯用捂着耳朵在榻上打滚的伎俩,从无败绩。
陪着曾祖母做手工活,其实是一段很枯燥的过程,只是镀金的环在塑料的孔里穿来穿去,为两个相隔南北的塑料片搭起横跨银河的鹊桥——曾祖母严肃的时候真像王母娘娘哩,我只敢在心里悄悄说。
“小燕子……”
“到!”我噌地来劲了。
“去剪一株荠来……”
荠被曾祖母养在窗台的中央——是一块精心选择的风水宝地,是一块会随着阳光移动的宝地。
望着眼前蓬蓬勃勃的荠,我兴奋的劲儿倏然便散了,放下剪刀,不由轻轻用指腹摸摸她。她抖抖身子,亲昵地靠向我,连额前的米白花冠都洋溢着明媚的娇憨。曾祖母也不催促我,似乎也忘了刚才的吩咐。
我喜欢和荠玩盲人摸象的游戏,荠是这方面的行家,总能找到我的指腹,坚定地贴上来,而我也不赖,清楚地知道——小小的光滑微皱是她的果,绵长着海岸线的心形;柔软如新生婴儿的是她的花,喜欢嘟着小嘴跟我说话;绒毛微微刺手的是她的叶,幻想着长出飞鸟的羽。
等我和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像爱曾祖母一样爱荠的时候,荠被曾祖母用剪刀亲自剪了下来——那是我第一次如此的心痛,连呼吸都是黄连般的苦恸,甚至连哭都深深地咽回了肚子。那是我的曾祖母啊。她将荠薄薄的果微微向下撕,不断,晶莹的纤维支撑着,轻轻一摇——那是荠第一次发出那么鲜活的声音,“叮铃叮铃”,她终于变成飞鸟了,可她在跟我告别。
我的泪终于留下来了,微微刺着我的皮肤,像荠的叶,像曾祖母的手。
没过几天,曾祖母要搬到一楼去了。装修人员忙着在家进进出出,将一楼的大会客厅隔开,改成一间卧室和一间厨房,到处弥漫着粉尘的颗粒味。
大人们不允许我找曾祖母玩了,可他们却天天带着穿着白大褂的人去烦曾祖母。我生气了,可再怎么撒泼打滚也不会有人买账了。
莫名地感觉不对劲,我偷偷地从杂物间搬来小椅子,垫在窗户下,从窗棂的缝隙往里望。曾祖母躺在高高的红木床上,灰色喜鹊被子大半落在了地上——还真是个小孩呢,我老气横秋地在心里叹道。
看四下无人,我掂着脚尝试拧了下门闩,开了!我不由放轻了脚步,慢慢挪到了曾祖母身边,爬到床上将那重重的灰被子往上提溜——被子真沉啊,精疲力竭后只想美美睡一觉。
“小燕子……”
依稀听到熟悉的声音在唤我,那似乎也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她在唤我了。
行李箱在平坦的水泥路上顺畅地滑着,轻而易举地划过了我的童年,长大似乎也只是一瞬的事。
但我看到荠的时候,我知道,她还在,不管这次寒假,这次春节,还是未来。
外国语学院 黄鸿烨 19850167312
褶皱里的春芽:乙巳年冬叙事诗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未完成的告别与正在生长的永恒
乙巳年正月的最后一天,我坐在学校图书馆的落地窗旁,看暮色将玻璃幕墙染成旧宣纸的昏黄。西斜的日影正掠过"2025年2月27日"的数字,像一把金箔尺丈量着寒假与春天的裂隙。《一本通》里掉出的车票蜷曲如茧,南京南至沧州西的铅字间,还嵌着钟山松针的碎屑。我忽然懂得时间的残酷与慈悲,它把相聚与永别、欢笑与泪水统统塞进了寒假里,如同孩童将四季花草粗暴地夹进日记本,却在多年后让人对着干枯的褶皱落泪:原来那些未登顶的高楼、未讲完的故事、未落下的告别,才是生命最隐秘的根系。此刻且让我蘸着黄昏的余温,在蛇蜕般的老黄历上,写下这场始于钟山薄雾、终于田野暖阳的成长叙事诗。
四年前父母在车站送我时,父亲摩挲着录取通知书附赠的旅游手册。玄武湖的波光在他皲裂的拇指下明明灭灭,“等有机会了我和你妈就去南京玩一圈”父亲说。这句话在秦淮河结了四次薄冰,终于在新雪初霁的早晨化开,我们沿着梧桐大道走着,母亲忽然驻足:"你姐拿通知书那年就说要来,现在她孩子都满地爬了。"母亲打开手机相册,我看着手拿录取通知书的姐姐和父母的合影,那时他们真的好年轻啊,此刻父亲鬓角的白霜在晨光中重叠,恍若时光打了个褶皱。
中山陵的392级台阶上,松香在风里酿成了液态的时光。父亲布满老茧的手抚过花岗岩,指节与石纹的褶皱在暮色里融成同一道年轮。我数着他鬓角的白霜,忽然惊觉这具曾为我遮挡风雨的身躯,早已被岁月压弯成谦卑的问号。
老门东的暮色稠得能粘住飞鸟。我带母亲去我很熟悉的店买糕点,店里人潮涌动,摩肩接踵,几乎让人寸步难行,但母亲始终紧紧牵着我的手,未曾松开分毫。这感觉就如同小时候她带我去商店时一样,她用那有力且温暖的手,牢牢地握住我,唯恐我走失在人群中。当秦淮画舫的灯笼次第亮起,母亲忽然轻声说:“要是你姥姥姥爷能来多好。”那时我们都不曾预见,这句叹息会在多天后化成灵堂前的白幡。
变故来临时我们正在鸡鸣寺看蜡梅。母亲接电话时,手机屏幕映得她瞳孔发蓝。返程高铁穿过华北平原,夕阳在车窗上烙出血色指纹。我望向车外落日,忽觉寒意袭来。
重症监护室的灯光在《刑法学讲义》上织就栅栏。姥爷的手背爬满输液管的藤蔓,监护仪绿线如早春柳枝轻颤。除夕夜的烟花映在病房的玻璃上时,我紧握着姥爷枯枝般手,和姥爷说,“姥爷,咱们回家了” 他手指在我掌心轻叩三下,像很多年前教我打算盘时的起手势。
初五的月亮是枚生锈的顶针,把姥爷最后的脉搏缝进夜色。在外守灵的我默默的跪在火盆旁,纸灰在孝服上烫出细小孔洞,如同他未说出口的遗言。
初八的晨光渗进窗帘时,姐姐抱着十个月的外甥跨过门槛。孩子脚踝的银铃铛惊醒了沉睡的堂屋,姥姥颤巍巍的手指抚过婴孩胎发,在阳光里扬起细碎的金尘。
而我,在这温馨画面前,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快门,定格下这美好瞬间。当我把这张照片发送至家庭群后,才惊觉上一条消息竟是姥爷出殡时的视频。我久久凝视着这组照片,它们宛如21世纪的《清明上河图》般,呈现出生活的丰富切片——一边是生命的起始,带着无尽的希望与活力;一边是生命的终结,充满着庄重与肃穆。
"这也算是新人换旧人了。"姐姐将温好的奶粉递给我,蒸汽在手机屏上凝成水珠,模糊了棺木与奶瓶的轮廓。窗外老槐树的枯枝突然爆出绿芽,某个瞬间我错觉看见姥爷站在树影里,正把襁褓中的姐姐举过头顶,如同三十年前某个相似的春日。
暮色中的手机突然震动,家庭群弹出新消息:姐姐带着外甥参加了宝宝快爬的活动,在姐姐的鼓励声与外甥的哭声里,恍惚间,我听见1958年姥姥绣嫁衣的顶针磕碰针线筐、2000年父母小商店开业时的算盘珠噼啪作响、2025年我的法考书页在病房陪护椅上翻动。
夹在《一本通》中的车票已褪成浅褐,南京南至沧州西的铅字却愈发清晰——原来所有未抵达的月台都藏着候鸟的磁极,所有未落尽的春雪都含着种子的裂壳声。
我望向窗外,玉兰苞裂开的刹那,忽然看清那些褶皱里的纹路——未登顶的高楼是父亲佝偻的脊梁,未讲完的故事是母亲攥紧的手温,未说出口的告别是姥爷最后的指叩。
重新收好车票时,图书馆空调暖气传来春汛般的轰鸣。我知道,在保定老家未化的春雪下,梧桐新芽正在穿透时光褶皱,而我要带着这些隐秘的根系,走向刑诉法讲义里正在苏醒的晨线。
法学院 韩枫 188517806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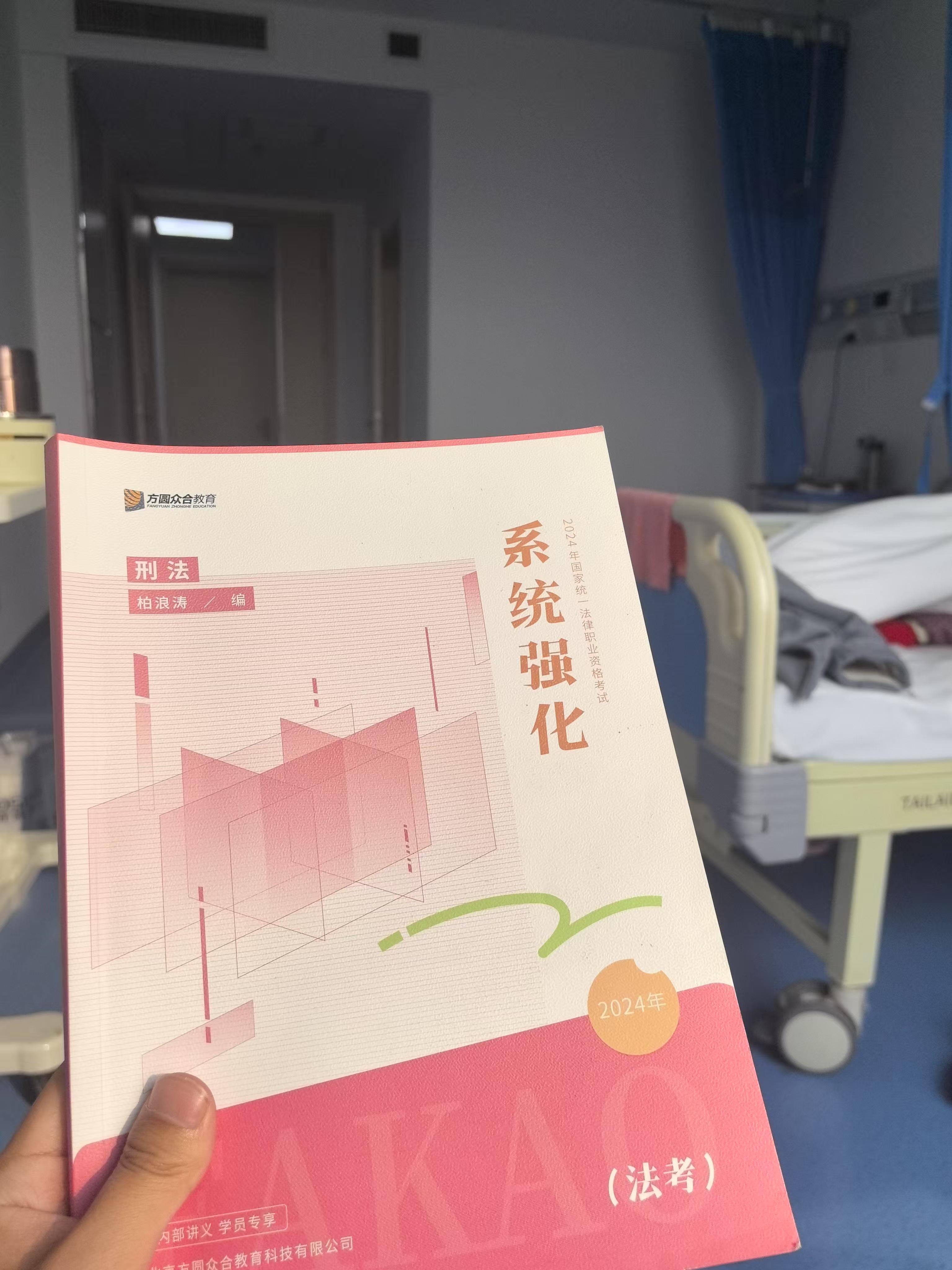
彩调绘新春
当最后一声鞭炮声从火焰中绽放,假期的脚步便无法追逐。父母的关切声慢慢地推着万千个与我一样的学子早日踏上返校之路。回程的高铁上,数个多彩的记忆在我脑海中翻涌着墨,绘制成独属于我的新春画卷。
画卷赭红:围炉夜话
老宅的八仙桌上,奶奶用布满裂纹的手揉着面团。蒸汽在玻璃窗上洇开,氤氲着荠菜猪肉馅的鲜香。“包褶子要像梳头,得顺着劲儿。”她将我的歪扭饺子摆成莲花阵,灶膛里柴火噼啪,映得老人银发泛起暖色。当父亲掀开冒着白烟的锅盖时,表弟突然指着窗外惊呼:“花!”原是腊梅在雪夜里绽开了第一朵,像落在枝桠间的火星。


画卷黛蓝:雪山明眸
除夕前夕,我们全家动身去了纯洁圣地——丽江。在第三日清晨泛舟拉市海。划桨惊碎镜面,忽看见远山正将积雪融化成的蓝倾倒进湖心。船娘说这是“天青过雨色”,我却看见不同层次的蓝在绸缎上流动:孔雀翎的幽蓝、唐卡矿物颜料的钴蓝、还有纳西族扎染特有的靛蓝。
画卷墨黑:书页叠影
最难忘是听雪夜读。读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台灯将银杏书签的影子投在墙面上,像极了太虚幻境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桌旁的姜茶热气里,书页上似有胭脂泪正沿着五百年前的墨迹蜿蜒至今。
画卷嫩黄:童声破土
寒假或许也是爱心的时节,在志愿服务社区幼儿园时,园下走廊的绿墙漆剥落处,竟是长出了春天。当我蹲下给孩子们系鞋带时,四岁的朵朵突然把冰凉小手贴在我脸上:“老师你的酒窝会开花!”他们画太阳总爱涂上七种颜色,唱《春天在哪里》时会把“红的花”改成“绿的云”。告别那天,小班长偷偷塞给我黏土捏的小花,嫩黄花瓣上还嵌着闪粉,像把整个正午的阳光揉进了掌心。画卷闭合,记忆与我仿佛不同天地,怅然若失。
整理行囊,发现速写本里夹着腊梅花瓣,绘本上还留着朵朵画的彩虹小熊……原来寒假从不是时间的断点,那些温暖的火种、清冽的泉眼、静默的生长,正在编织成新的经纬。
此刻静默宿舍阳台,我见玉兰正含羞,忽然懂得:所有冬天的色彩,原是为了在春天挥洒更斑斓的轨迹。
人文传媒学院 董叶 18762015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