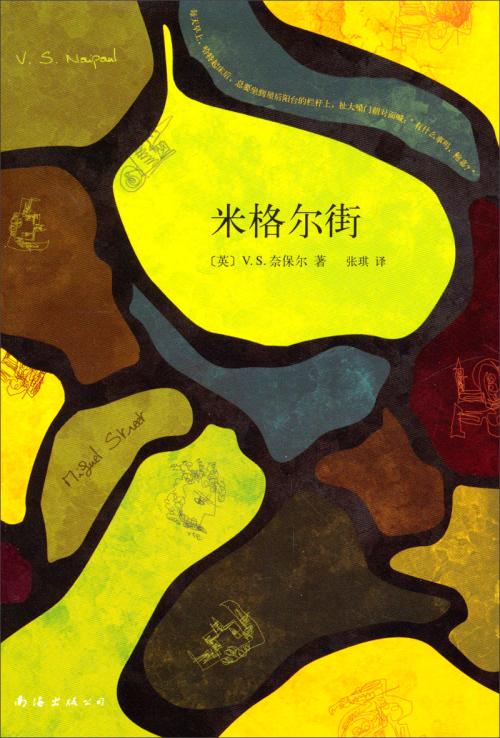
《米格尔街》由十七个平行展开的短篇编制而成,每一篇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相同的人物在不同的小说中重复出现,相互指涉,形成片断与整体、串连与复现相结合的互文结构。
奈保尔把故事的发生地点固定在特立尼达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上,那里贫困、脏乱。这种将人物、故事等固定在一个特定区域的叙事方式,会令人不自觉地想起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和鲁迅笔下的未庄。马孔多、约克纳帕塔法和未庄都是作家虚构的地方,米格尔街却是奈保尔生长的地方,但是亦不能因此就断定确有米格尔这条街,在《注册会计泰特斯?霍伊特》中,作者写道:“可是,我却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我找到了差不多六条叫米格尔的街,可是哪条街上都没有我家的房子。”所以,与其说米格尔街是一条实实在在的街,还不如说,米格尔街只是奈保尔成长环境的一个代名词,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市井社会一幅真实的风情画。这条街上的一切并不新奇,在特立尼达,到处都是这样的街。那么即使奈保尔的写作是依据了自己的经历,这些小说也不会因此而失去普遍的意义。
《米格尔街》好读、真实、质朴,当然好读并不代表它的意义浅显。在这十七篇小说里,充满了断裂性。故事中所体现出来的断裂性,首先表现在一种弥漫于全篇的孤独感,人与人之间交流障碍上面。
在一开篇的《博加特》中,奈保尔就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孤独、间隔的信息。“我所认识的人中他是最乏味的”,而所谓的乏味是因为他“总是低着头闷声不响”“从不笑出声来,也从没讲过什么故事”,博加特很神秘,因为他“平时很少对他们吐露什么”。虽然大家都觉得遇到什么喜庆日或其他重大时刻,可不能少了“博加特”,实际人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相互了解。而《米格尔街》中所涉及到的夫妻关系问题,也集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境。在文中出现的众多人物中,没有一对是婚姻幸福美满的。博加特重婚又将新妇遗弃,波普的老婆离家出走,布莱克·沃滋沃斯幻想并不存在的爱情,墨尔根太太是“母老虎、西班牙婆娘”,比哈库拿老婆出气,爱德华被骗被抛弃,海特与多丽“是街上最古怪的一对”,虽然他们从未吵架,却像“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自古以来,爱情都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是人人向往的最美好的事,爱情可以消除两个人之间一切的孤单寂寞,让彼此感受到支持的力量。可是在奈保尔的笔下,爱却与孤独共存,或许爱同时也制造了孤独。
谈到奈保尔就不可不谈他自身的移民经历,也正是他独特的成长历史和他身上的文化的断裂性,使得他的笔下总有那么一股深埋的孤独。
众所周知,奈保尔是一位移民作家,在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辞里,他被称为“一个文学世界里的漂泊者”。他的祖父1880年作为契约劳工从印度北部漂洋过海移民特立尼达。奈保尔年幼时,父亲凭自学谋到特立尼达英语《卫报》记者之职,于是举家从乡间小镇搬迁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而在1950年,他又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牛津大学的奖学金,自此前往英伦,开始了新的人生。于是他成了特立尼达的“流放者”,英国的“外来者”,印度的“海外浪子”。从印度的贵族传统到特立尼达的殖民文化再到英国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奈保尔陷于的并不止是两个世界,面临的也不止是双重性,而是多重世界与文化多重性。于是他感到了自由也因此感到了无根的失重,产生了自我身份认同危机: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将去向何方?这些问题也成了奈保尔小说中的中心话题。其实不止是奈保尔本人面临这样的问题,整个特立尼达,所有被殖民多年而又面临独立的前殖民地区的人们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文化强行进入多年以后,突然的断裂使得一切都不再自然,传统已不复存在,西化也不过是表面现象,是该向传统回归还是追寻着西方文化的足迹,这是个问题。因此,奈保尔的小说具有了普遍意义。
在出身于异化的环境并且要思考如何认识和应付这种异化的过程中,奈保尔也曾充满疑惑。在《抵达之谜》中,他回忆说:“我在特立尼达岛以一种不太可能的方式接受了十九世纪末美学运动的思想和布卢姆斯伯里的思想,为了成为那种作家,我只能变得虚伪起来,我只能假装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假装自己是另外一种背景下长大的人。”奈保尔本人表达的已经很明确了,为了写作,他试图丢掉自己的背景,去模仿别人的生活。“‘模仿’的效果就是伪装,它不是要和背景协调一致,而是逆着杂色斑驳的背景而变得斑驳——特别像人类战争中的伪装技术。”奈保尔本人的模仿行为也体现在了他小说中的人物身上。《博加特》的同名主人公原名“佩兴斯”,电影《卡萨布兰卡》走红特立尼达之后,米格尔街上的人都用电影中主人公的名字叫他“博加特”。这个沉默的人,在离开米格尔街又回来之后成了“街上最令人胆颤的人,甚至连大脚都承认害怕他”。而在第二次离开又回来以后,他“讲着一口地道的美国腔英语。兴许为了使自己的模仿更加逼真,他开始向孩子中间扩张。”《直到战争来临》中,战争爆发后,“爱德华彻头彻尾地投靠了美国人。他的衣着越来越美国化,还学会嚼口香糖,就连说话也拼命撇美国腔。”模仿一直是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反殖民主义者所采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抵抗形式。但这些可笑的模仿是对可以确定的文化的向往,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迷失,模仿不能解决新独立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无论怎么模仿都改变不了他、他们那“他者”的身份。
值得庆幸的是,奈保尔很快就认识到了,“在作家身份的掩盖下,隐藏印度侨民血统的做法,无论对我的素材还是对我本人都带来很大的损害。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拼命地想找到一个答案:作为一名作家,我所需要的可能是什么样的素材。突然有一天,我眼前豁然开朗,我茅塞顿开”我非常简练、快速地写下了我记忆中最普通的事情。我写了有关在西班牙港的街道,我的童年生活曾有一段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在奈保尔以后的作品中,尤其是《河湾》一书中,他仍在继续着追寻的主题,但是此时的奈保尔已经能够用比较平和的心态区面对自己的出身,面对无文化之根的现实。不用抛弃自己的背景,不用模仿别人,表现出自己的本色特征,不带偏见的为自己,为后殖民地区的人们寻找未来的路,真诚的写作,事实证明这才是一条长远之路。
《米格尔街》只是奈保尔五十多年创作生涯的起点,但是这一起点却极有高度。瑞典学院的诺贝尔授奖词中也特别提到这部作品,说其中的短小故事“把契诃夫与特立尼达民间calypso小调结合在一起,奠定了幽默作家和街道生活讲述者的名声”。奈保尔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一颗敏感的心。在《米格尔街》里他者揭示了第三世界人们的普遍困境,他的描写无情而又真实,使读者看到了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生追求的多样性。由此或许我们可以说多样性正是后殖民地区人们的存在方式。虽然,孤独弥漫在米格尔街上,可是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奈保尔对归宿的渴望,对文化家园的追寻,感受到他——一个处处无家处处家的“世界公民”——的思索与启悟。
(来源:豆瓣)



